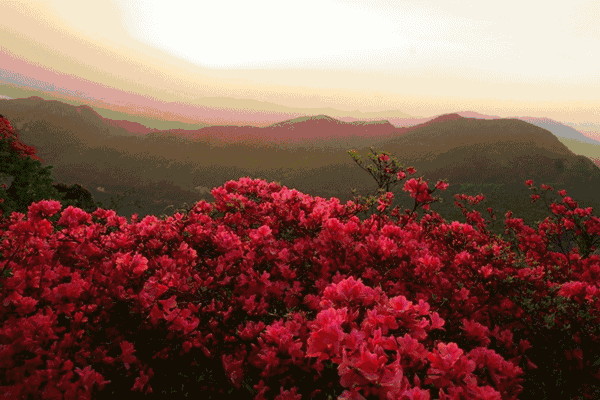來源:瀏陽文旅
大圍山的杜鵑的確很美,換乘的大巴從中轉站緣著正在修建的公路往山頂開了十幾分鐘,車廂裡的乘客都迸發出訝異的驚歎,順著他們指的方向,只見遠方的山嵐簇擁著紅色的火焰,再過十來分鐘,車子就完全融入那片火紅的海洋之中,眾人開始沸騰。此時,怕皆有那種恨不能將身化作千千萬,一樹杜鵑一放翁的遺恨了。
在眾人皆熱烈著奔跑追逐之際,我倒希望自己趕快靜下來,希望自己放慢步子,數十裡連綿起伏的山脈迤邐而去,全飄搖著紅色的波瀾,全是杜鵑妖豔的海,想擁抱,想疾呼,甚至想在那花叢之中翻舞打滾,如此折騰一番,終將發現想擁有的這一切,只屬於大圍山,激烈之後,難免會惆悵,會蒼茫,會有失落。
此時,有爛漫的杜鵑,有曲折棧道,有臨風涼亭,有藍天白雲與輕風,有可資遠瞰的峰巒,當慢,當把自己從那世間的嘈雜之中慢慢分析抽離,給自己一個平和的心境,再慢慢融入到這花海中來。是時,簇擁的花海是帶不走的,倒可把自己也想像成那一抹亮麗的紅,在紅色的海洋中隨風飄搖。爾後,那山花的熱烈,自會流入到你的胸膛中來,說你在花海中徜徉,其實花海亦在你心中流淌。
來大圍山之前,《大圍山》雜誌的執行主編謝利文囑我寫幾句,我根據我對大圍山的印象謅了一段,其言曰:大圍山,是夢的故鄉,是心靈的棲居之所;這裡,遠離塵世的喧囂,留給世人十萬大山,十萬綠色的海洋,這裡有茂林修竹,瀑布與潺流;有勝似蓬萊的雨後仙境;有萬畝杜鵑與草徑通幽,請原諒這裡還沒來得及車馬喧嚷,沒來得及澆灌鋼鐵叢林,請原諒這古拙樸素,原諒掬水而飲的酣暢,這裡能給你的,真的止有這麼多。
但具體與我說大圍山杜鵑如何好的,是李海,說了很久,其實我終究沒有親眼見到,而別處的杜鵑早就從遊客如織到落英繽紛甚至空山寂寥了,偶爾按捺不住催促,得到的答覆總是說快了,快了。如是數次,自以為錯過了花期,正為此事悵惘時,李海卻在春天的最後一個晚上打電話來,說是此時才是杜鵑開得極盛的時刻,他們計畫借機主辦一次‘賞花大圍山’湘潭瀏陽兩地書畫名家藝術交流會,並邀萍鄉上栗的一干藝術界朋友作特邀佳賓一同前往。
這是第二次應邀參加大圍山的文藝活動,兩年前曾借文藝之名到瀏河源參加漂流,那日接待的莊主陳觀生亦是一位在書法上很有造詣的方家,此次賞花,他亦作為瀏陽方的書法家同行,此行湘潭有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張德義,《中國書畫家》雜誌中南分社的編輯符陽明與胡永強等人,萍鄉有赫東軍與朱述萍等人。
這樣一干藝術家,有耄耋老人,有矜持長者,有敏感的詩人,有筆底生風的畫家,在這樣浩瀚起伏的紅色山嵐裡折騰一回,其心中的浩瀚,怕是只有酒能撫平了,返回山腰下榻的森林賓館,客人們皆把這本應含蓄表達的渴望大聲嚷了出來,很有一番古典小說裡的武夫把腳踏在板凳上大喊‘店家,拿酒來!’的慷慨氣勢。遺憾的是主辦方僅在桌上備了四瓶啤酒,面面相覷的客人們略感尷尬,幸而湘潭那一桌的某位善飲者在其中廂中備了數瓶穀酒,我們萍鄉那一桌也分得了一瓶,只能算小酌。
帶著略許的醉意回到房間就接到李海的電話,數分鐘後,一桌人馬又浩浩蕩蕩奔往山腳的大圍山鎮,李海說是回自己的第二故鄉看看,十數年前他曾在這裡做過兩年的副書記,其實大家都知道,他是要帶我們去補回剛才那小小的缺憾。那個夜晚,大家著實狠狠地補回了晚餐桌上那小小的遺憾,只有我辜負了大圍山鎮那位朋友的美意,大家在KTV裡惡補時,我開車到山腳下看月亮。
山區的月亮與都市的月亮是很不同的,巍峨的大圍山頂,月光有著恬靜之美,什麼是十萬大山?就是這原始的深邃與曠遠,這仰望,這極目之處的大寧靜,月與山齊,與輕淡雲煙的廝磨,是山給了人以寧靜,給了月以寧靜。山風激蕩,流水輕鳴,月的光芒是羞澀的,東門橋上,徘徊的我,突然有了遺世而獨立的滄桑感,許是此時的唯美與往日的嘈雜帶來的巨大落差給了我這種感覺,亦有可能是這月夜孤獨地欣賞美而給人以蒼涼。
看來,我還是醉了,許是剛才的小酌給了我足夠的餘韻,許是這山花的熱烈與夜之柔美讓我情不自禁…
作者簡介:楚山,江西萍鄉人。著有散文集《月落楚山》及《思念在燭光下誕生》。